人終極的「詩與遠方」
/ 在人生的詩意中遇見神 /

▲作者李文屏在「擺脫」號遊輪甲板上。
「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,還有詩與遠方的田野。」不久前,此歌一出,大眾心弦為之一動,「詩與遠方」一詞迅速流傳,表達了人心中那難以言說的悸動。它是甚麼意思?真的是「詩」與「遠方」?
至少有時候是。
同一地點下船,到達不同彼岸
今年(2016)5月22-29日,我有了一次名副其實的「詩與遠方」之旅,因為出發是為了詩,在挪威遊輪公司(Norwegian Cruise Line)的「擺脫」(Breakaway)號遊輪上作詩歌講座;而且真的是去遠方—先從太平洋西岸飛到大西洋東岸,再從美國大陸到英屬小島。
這個「遠方」似乎還有點危險,因為目的地是百慕達—「百慕達三角」那個百慕達,世界聞名的飛機輪船神秘失蹤之地。雖然「百慕達島」不等於「百慕達三角」,但出發前還是有朋友聞名色變,跟我開玩笑。信主的說:「請替我問耶穌好,我表現不太好,但其實挺愛祂的!」不信主的說:「哦,啊,妳膽子夠大啊!」
上了「擺脫」號遊輪,感覺這船的名字取得好,為乘客的心情做了導向:擺脫日常生活的枯燥與繁瑣,到達美麗而快樂的遠方,實乃「逍遙」號也。船行三天到達目的地時,一個笑話從記憶中浮現:一名甚有優越感的人上了飛機,持有經濟艙的票,卻非要坐在頭等艙的空位不走,空服員百般勸說,無效,只好請機長出馬。機長和藹地問:「你要去哪裡?」答曰:「紐約。」機長於是對那人耳語了一句話,那人聽後立刻起身,匆匆回到自己原來的座位上。空服員們大感驚奇,機長密語了甚麼,這麼有效?!機長說:「我說頭等艙是到舊金山,經濟艙才去紐約。」
這是諷人智商的笑話,但我發現這個笑話放在這艘遊輪上,還蠻有道理。為何如此說?
上了遊輪,彷彿進入大西洋上一座漂浮的小鎮。鎮民形形色色,鎮上生活總體來說卻只有兩種:一是離開家園,吃喝玩樂;一是離開家園,服事人玩樂吃喝。
但這中間有一群奇怪的人,他們不太理會花錢買來的船上娛樂,穿過形形色色的賭博老虎機和牌桌,上午在一起靈修、敬拜神;下午在一起談詩論畫、寫詩作畫;晚上剛開始也去看船上劇院的節目,但那注重感官刺激的節目,對他們而言,似乎很缺乏刺激性,他們中好些人打起瞌睡來,後來乾脆不去了,寧願三三兩兩,一起分享、散步等。同在一艘船,他們似乎在看不同的風景,享受不同的盛宴,到達不同的港灣。
我感覺這遊輪很像現實世界的縮影,同樣在世一場,耶穌基督的愛和對祂的愛的不同回應,將人的路途和目的地都分別開了,就算在同一個地點下船,到達的也是不一樣的彼岸。
甚麼是你我的彼岸?或者,甚麼是你我的「詩與遠方」?
那麼具體點,到底甚麼是人的「詩與遠方」?
騰訊數據顯示,微信用戶至2015年3月底,已達5.49億,覆蓋智能手機用戶的90%。從微信流行的故事,我們可以管窺人們共同的「心事」。
前不久,我接到幾次推送,分享的是同一內容:一位模特在四十歲時退出時尚圈,回歸鄉村作農婦,種植莊稼,養了幾個孩子幾條狗。分享的朋友覺得這個故事充滿詩情畫意,覺得此人的生活值得羨慕。我問:如果這位農婦不是模特轉身而成的,你還羨慕嗎?答案是:「嗯,好像不會。」那麼為甚麼同為農婦,本來就是農婦的農婦生活不值得羨慕,模特轉身的農婦生活就值得?
究其根本,我覺得是因為本為農婦的農婦,她們的生活往往是只能如此,屬於命運安排的不得已,也就是「苟且」;而模特轉身的農婦生活,是種主動選擇的喜歡,是自由的體現,是夢想的實現,所以值得羨慕,是「詩與遠方」。

▲2016年4-5月期間,微信公眾號流行推送關於一位模特轉為農婦的文章。
「詩與遠方」之所以撥動人的心弦,因為它象徵了更美好的夢想,讓人與「眼前的茍且」—那份生存的不得已—對抗。羨慕這位前身是模特的農婦,不一定是羨慕她的農婦生活,而是羨慕她田園夢想的實現。
「詩與遠方」就是這麼具有蠱惑性,所以「說走就走的旅行」也成為一種普遍的嚮往,它所蘊含的那份自由讓人眼睛發亮,似乎「說走就走」,真的可以到達「詩與遠方」。為了那份自由感,有人真的說走就走了—從工作中或從關係中出走,可惜未必能到達「詩與遠方」,反而淪落到加倍的「苟且」裡。因為「詩與遠方」不是靠表面的或一時的瀟灑就可到達,它需要人付出切實的努力,具有必要的實力或條件。不過這些現象卻都表明,自由而美好的生活(亦即「詩與遠方」),是人們共同的嚮往。
還有那些老年人的精彩故事,比如八旬奶奶跳交際舞,還在空中、地上翻騰,把人嚇得張口結舌,隨後拼命鼓掌點讚;比如年邁才學畫的農婦摩西奶奶,結果成了《時代週刊》的封面人物,大獲成功。為甚麼我們喜歡這樣的傳奇?因為這些老人家敢於藐視「合情合理」的局限,比如血壓、心率、骨質、腦細胞老化等,向我們展示了甚麼叫活出夢想—在現有的局限下,持有一份不羈的自由,敢追求,敢投入,付出努力,並樂在其中,還取得了成功。她們觸動我們內心深處對生命力的尊重,讓我們為之動容。

▲老人場中表演「驚嚇」了裁判和觀眾,收穫滿場尊敬、尖叫和掌聲,直接進入半決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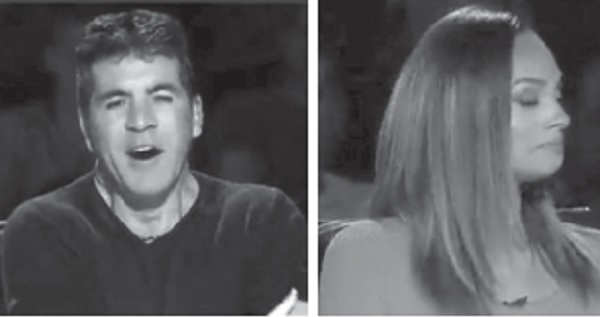
▲跳舞的英國八旬老人,上臺時面對裁判質疑的態度,回答提問。
而這樣的詩與遠方甚至可以出現在監獄裡。作家余秋雨在一文中提到,他曾去監獄演講,想順便探望一位為囚的朋友,但沒見到,就留了一張紙條:「平日都忙,你現在終於獲得了學好一門外語的上好機會。」幾年後朋友出獄,神采飛揚,帶出一本六十萬字的英文譯稿,準備出版。
可見,詩與遠方不一定在遠處,也不一定只在充滿詩情畫意的地方,只要內心仍有選擇的自由,能夠投入夢想,就算有環境的限制,也能將日子過得充實而富有意義。這就靠近了詩與遠方的本質,就是走在通向詩與遠方的路上。是不是擁有詩與遠方,環境不是決定因素。
「詩與遠方」的暫時性
然而問題來了,因為起初想要的詩與遠方,到達後可能成為新的苟且,比如婚姻,比如移民。曾讓人有動力跨越千山萬水的地方,最後為甚麼成為盛行的雞肋、嘆息,甚至內傷?
還有成功。著名作家傑克倫敦歷盡千辛萬苦得到公認之後,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:山頂其實沒有想像的好。
最有詩意的應該是詩人了吧,但一些成名詩人們的自殺說明了甚麼呢?難道是說生活中構成詩的詩意不具有支撐生命的能量?
還有名校,多少華人父母認為那是兒女通向「詩與遠方」的專車,甚至是「詩與遠方」本身;然而達到後的學生們,為數不少並非生機勃勃,而是抑鬱焦慮,罹患心疾。作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公立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,壓力指數也是全球大學中數一數二的,其校園的標誌性建築—307英呎高的鐘樓,因有學生在那裡自殺身亡,特別安裝了安全設施,以防更多悲劇發生。
而出名呢?出名往往是成功的標誌。許多成功的名人,尤其在演藝娛樂界,外在生活似乎充滿光彩和詩意,內在卻難免滿懷滿抱的苟且感,不堪忍受者多有轉向毒品,甚至放棄生命者。
為甚麼我們孜孜以求的東西最後會變質?夢想為甚麼會變成苟且?有沒有值得追求的終極的「詩與遠方」?

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標誌性建築Sather鐘樓,因有學生在此自殺而安裝了防備措施。(攝影:Tristan Harward,來源:Wikipedia)
詩心的萌芽
有人曾問我詩意從哪裡來?這時我腦中往往出現一幅圖畫:穹蒼之下,群山之中,一名小女孩紮著兩條小辮,在山坡上戲耍,時不時驚艷於那些平凡而美麗的山花、偶爾發現的野莓、山澗飄逸的白霧,還有遠方的落霞,腳下的青石,以及耳旁各樣的蟲鳴……。那是貴州一處貧瘠、偏僻、多有灌木少有喬木的地方;但對那名小女孩來說,卻充滿了各樣的趣味,日子是那麼新穎有意思。
那個小女孩就是童年的我,在文化教育與經濟一樣遠遠落後於大部分中國的地方,詩意卻早已生根。一年甚至不能吃到一顆蘋果的物質貧乏,從來沒有掩過山風流嵐帶來的莫名的喜悅與感動。那樣的感動溫和地蕩漾在天地之間,隨著四季的從容轉換,漸漸在我心中匯成一種需要表達的生命的湧動,那就是詩意。
於是,小學二年級的一個午後,我坐在爸爸搭的油毛氈屋頂上,曬著太陽,開始塗鴉詩行。寫的是甚麼我早忘了,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不成其為詩,只記得寫時的寧靜、愉悅和滿足,還有那溫煦的陽光如何照在我的背上、頭上,溫溫熱熱的,像我的內心。
當一個人心裡詩意蕩漾的時候,無論他/她的文化水準如何,掌握了多少語彙,懂不懂得表達,物質條件怎樣,年齡幾許,他/她的生命都是豐沛而蔥蘢的。那一刻的時光真是品質非凡,那是「詩與遠方」的品質。
所以如果問詩意是怎麼產生的,我可以本著個人體驗說,它來自造物主。造物主用祂對自然的詩意的創造,潤物細無聲地喚出了祂早已賦予人心靈的詩意。
九〇年代初,我已大學畢業開始工作,參加了第一屆艾青杯世界華人詩歌大賽,蒙評委錯愛得優秀獎,獎盃由我自豪的公公拿去保管了,詩歌手稿則因出國及多次搬遷而不知遺落何方。我甚至不記得寫的是甚麼,不過記得同期的一些詩句(可能出自該詩),比如:
遠方在死
白天鵝在垃圾漂浮的護城河上默然
像句悲哀的悼詞
又如:
生者拖著長長的影子
死者閉上眼
向生者默哀
「遠方」也是我詩中的意像,但卻「在死」。那份生命的沉重感,最終一度導致我內心詩意和外在創作的終結。我想,偉大的文學都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深刻反映,而人生與社會本來已如此不堪,何苦再用文字來重現?寫作實在是沒有意義的!
然而後來還是詩筆再提了,認識了耶穌基督後,那失落的詩意不知怎麼就重新流淌了回來,連同兒時對生命的驚奇和喜悅,彷彿封閉的囚牢開了門窗,有對流的清新空氣迤邐而來,源源不絕,以至在我甚是艱難的日子裡,只要能注目耶穌,就有寧靜而祥和的詩句湧出內心;而不能注目耶穌時,那就真是很遭罪了。

▲穹蒼之下,群山之中,作者李文屏的家鄉所在地。(攝影:李忠屏。)
詩意的根源
所以若問詩意是怎樣產生的,我也可以翻看著自己寫下的詩章說:詩意來自生命之源—上帝。在安靜的角落,我看見祂的微笑,因此在呼吸的豪華裡,有生命的奧秘向我啟迪。我知道上帝之手觸摸過的地方,就有好花綻放。這,讓我安心,感覺無論順逆,「有祢陪伴,我多麼願意在光陰中行走。」(見拙作《百合花開放的那天》)
這失而復得的詩心,讓我明白:詩意可以是短暫的,但若有了永恆的根源,它就能夠回歸,可以持續。今天,詩甚至成為我靈修的方式之一,幫助我體會神所賦予的生命的詩意。
勞瑞‧克拉布(Larry Crabb),暢銷書作者、心理學家、美國基督徒心理輔導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Counselors 的屬靈指導,曾因腹部腫瘤住院。他站在醫院的窗前,看到對面的星巴克,浮想翩翩,覺得不公平,對神抱怨。神對他說:「如果我給你你所要的一切,但是沒有我,你要嗎?」他突然發現,如果他擁有了一切而沒有神,那是多麼可怕!換句話說,沒有神自己,哪裡有甚麼真正的「詩與遠方」?所有的到達和擁有,最終都是苟且。
在一次旅途中,我接到一位朋友的電話,說:「我只問一個『小』問題—甚麼是人生的意義?」有機會停車時,我發了一張路途的照片,回答她的「小」問題:「人生意義就在路上。」她以為我在開玩笑,其實我在說真心話。我們尋求甚麼,是因為還沒有得到;而當我們進入目的地後,我們就不再尋求了,而是靜享其中的過程。
意義就是這樣的東西,進入意義,就自然不再尋求它。我現在是已經行在人生的意義中—人生命的來源、生命的依靠、生命的皈依,即神祂自己,「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,倚靠祂,歸於祂。」(羅11:36a)所以我不再尋求意義,而是行在充滿意義、與祂同行的路上。
這不僅在於平時的生活,旅行也如此,我認為自然是上帝親手建造的聖殿,流連其中也是對祂的回應和敬拜。

▲作者李文屏在路上。喜歡旅行的她,認為生命就是心旅、靈旅和身旅的過程,以「在路上」與神同行為「甚麼是人生意義」的答案。
神對人生命的詩意規劃
世界上有太多的苦難和折磨在扼殺詩與遠方,但如果有自在永在的神為詩與遠方,有甚麼還能將我們的詩與遠方奪去呢?
而神對人生命的設計也原本如此,就是活在祂的豐盛裡,以感恩的心享受祂和祂所賜的恩典與福分。那樣的生活有一個詞可概括,叫「伊甸園」。神對人生命的詩意規劃只有一次,不過有兩次詩意的呈現。
第一次是創世時,神憑著自己大能、創意和愛心,無中生有,為人打造了詩意的生活環境及田園生活。那時,神是人的父母,是「親情關係」,而非「清單關係」—開出需要事項,讓神來滿足;自然是神為人預備的家園,美麗富饒,人能享受與管理,而非掠奪與踐踏(現在多少人進入城市,其實最終乃想回歸田園,彷彿創世時的藍圖,留在人靈魂中成為隱約難以明說的記憶);同時,他人是愛的對象,亞當夏娃相愛無猜,而非疏離、轄制甚至相仇。
可惜好景不長,人運用選擇的自由將自由弄丟了,所以有了神對人心意的第二次呈現,即耶穌基督的救贖。
這裡需要提一個故事:一位本來美麗的公主,因受一古老詛咒的轄制,失去了美貌與自由;如果公主要恢復身份和自由,必須有一位愛她的王子願意代替她的位置,甚至捨去生命,才能將她換回。而王子因為真愛,真的這麼做了!
對這樣的故事你是否感覺太熟悉太沒新意了?這是有原因的。這原是動人心弦、富有詩意的故事,人間忍不住以不同的版本來反復傳唱;唱多了,就成了老生常談。
但現在我們需要將這個故事的刻度拉大,時間拉長,放進永恆,填進所有的情節,它就變成一部宇宙的愛情史詩,就是聖經記載的故事:神的兒子耶穌,為了所愛的人類,放棄了自己身為宇宙之主的尊榮,來到世間為人所踐踏、唾棄,明明有大能卻不使用,為的是讓祂所愛的新娘—信祂的人,也就是教會,能夠被換贖回來,重新具有神所賦予的美麗,從死亡的詛咒中得解脫。
在我看來,這救贖的故事似乎是所有王子捨命救公主那種童話故事的最初藍本。動人的愛情童話似乎擺脫不了這個架構,是否是因為它像防偽的水印一樣烙在人的靈魂裡?
基督的救贖,是要讓詩意回歸,是要賦予人選擇自由的自由,因為在死亡沒被破除、靈魂不能回家前,人的一切嘗試都是苟且。

▲創世時,神憑著自己大能、創意和愛心,無中生有,為人打造了詩意的生活環境及田園生活。(The Garden of Eden,畫家: Thomas Cole,來源:Wikipedia。)
人終極的「詩與遠方」
以上帝為終極的「詩與遠方」的人,往往呈現出極大的自由。他們可能不寫文字的詩,但是自己的生命卻往往是詩意洋溢的篇章。
一位已去世的老姊妹,因我去她所在教會講道而相識。記得走下講臺,她像慈愛的奶奶般親吻我的臉頰—華人中對初識者少有的愛的表達。她醫術高明,為人善良,為病人和同事所尊愛,人生卻有很深的不幸,但她在基督裡選擇了饒恕和愛。我在她身上看到的是慈愛、寬闊和大氣的詩意。
一位年邁的師母,每月從微薄的養老金中抽出部分來支援宣教士,常常為宣教士禱告。我在她身上感受到的是富裕、自在和平安的詩意。
一位牧者領袖,平時注重關係,愛開玩笑,在癌症迅速擴散時也不例外,找機會與每一位同工和朋友一一話別,其追思禮拜中得到的禮金,也全數奉獻,用來關懷同工生活。我在他身上讀到的是智慧、幽默、體貼的詩意。
一位生病的姊妹,多年來身上的女性器官幾乎都被摘除了,進醫院像去超市一樣;可是她的喜樂那樣明顯,全身洋溢著健康的氣息,充滿生命的喜悅與光輝。她的笑容是那麼富有詩意!
這些以神為終極之詩與遠方的人,就是這麼富有生命的詩意。他們也有起伏、掙扎和乏力的時候,但因為神的無處不在,所以他們的詩意和遠方不會離棄他們,而是不離左右,甚麼時候轉向神,甚麼時候就擁有它。
一位在矽谷工作的弟兄,鬱鬱不得志,老闆還要他培訓用來取代他的人。他在內心轉向神之後,決定為神做而非為人做,於是變得開心而大度,結果培訓完後,老闆給他意外的提昇。當然不是任何人都會有這樣的經歷,不過任何人都可活出神所賦予的生命的命定—無論你是模特或農婦,老年或年輕,自由或受限,男人或女人,白領或藍領,領袖或員工,在基督裡都有詩與遠方。
而在基督裡,即是一切由基督罩著,我們全然交託,只放心地負責作祂呼召我們作的那個自己,因為生命是本於祂、倚靠祂、歸於祂。活在這樣的真理裡,人就擁有了生命的活水源泉、生命的不倒支柱和生命的溫暖歸宿。
願神成為你我終極的「詩與遠方」。

▲以上帝為終極的「詩與遠方」的人,往往呈現出極大的自由。在光陰中行走,無論順逆,都有彩虹。(圖片:Tomwsulcer and Haley Sulcer,來源Wikipedia。)
 作者小檔案 李文屏,認為自己是旅者,生活是旅行—身旅、心旅、靈旅,旅程亦是目的。她亦有其他頭銜,如作家、詩人、文字工作者,本刊執行編輯兼網站設計師,曾為廣播節目編導與主持。
作者小檔案 李文屏,認為自己是旅者,生活是旅行—身旅、心旅、靈旅,旅程亦是目的。她亦有其他頭銜,如作家、詩人、文字工作者,本刊執行編輯兼網站設計師,曾為廣播節目編導與主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