轻松一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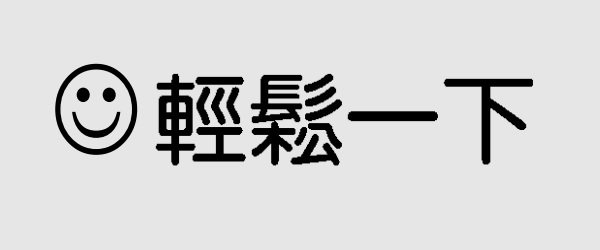
文字营期间,被苏文安老师训练眼观四面,耳听八方;感觉好像Peter Parker 变成蜘蛛人,一切感官全敏锐起来。近视眼变透视眼、瘦鸡变洛基(席维斯史特龙的那个Rocky)。但是,唉,生来一只重听的右耳还是没醒来,还有我那「出类拔萃」的中文,制造了许多笑料⋯⋯
给我出糗的耳朵
培训班报到的傍晚,大伙儿吃粽子喝莲子汤时,俐理姊发了一张卡片,说是要写给一位正在赶路过来的姊妹:「请大家签一下这张卡片,Amy今天生病⋯ ⋯」我才吃完,正要出门溜达溜达,也没听完俐理姊之后说些什么。回来后拿起卡片,洋洋洒洒写了一句:“Please get well soon!”(请早日康复!)
终于,Amy,也就是月娥姨,拖着个小行李风尘仆仆却精神饱满地赶到。 「她气色很好嘛,没什么病容啊⋯⋯」我纳闷着。忽然看到她右手包了一层黑黑的医护棉套。是啦,大概是她手有什么不适吧。晚上十点多后,课程结束了。俐理姊这时端出了一个生日蛋糕:「来,我们为Amy切蛋糕唱生日歌⋯⋯」不会吧!我吓了一把冷汗,是不是把生日听成生病了?惨了,人家好好的过生日我居然祝她早日康复⋯⋯唉,希望月娥大人不记晏君过,不要生气啰!
请问「蟑螂」怎么走?
培训班结束后,我不自量力地自动升级上进深班。有一天要拍团体照,大家约好照相地点在倚着绿山坡、诗情画意的修道院长廊。拍照时间快到时,瑞怡姊妹突然把我叫住问了一句:「蟑螂怎么走?」什么?蟑螂? 「嗯⋯⋯」我歪头很快地回想小时家里的南美飞天蟑。 「蟑螂这样走⋯⋯」我缩着头,张开双腿双脚,前后摆动走了几步,一脸畏畏缩缩的龌龊样。瑞怡大笑了起来:「我问妳长廊怎么走,不是蟑螂怎么走。」真是的,我这烂耳朵专给我出糗。
吃蚝油谢天恩? !
还有一次,艺术营的美学家们开结业画展。我一眼就爱上了邱建勤弟兄画的「天天有神恩」。鹅蛋黄的长玻璃窗前,有红番茄、绿青椒、白糖糕、土番薯口味的棒棒糖在飞舞,四周一大群伴舞符号也加入这场盛宴,热闹快乐得不得了。我把邱画家找来,请他为我解释那些符号的意义:
「请问这是什么?」我手指着三粒钮扣问他。
「这是红绿灯,感谢神保守我出入平安。」
邱弟兄操着一口越南广东腔答道。
「那这个咧?」
「这个是房子,代表神给我一个温暖的家。」
「噢,那这只红公鸡是什么意思?」
「嗯⋯⋯这是玫瑰花,不是鸡。」
玫瑰花又代表什么,我不敢问,把他的花看成鸡已经很不好意思了。
「这又是什么?」赶快转移主题。他画这三条弯弯曲曲的线,我看不大懂。
「WORO…」他咕噜咕噜地说。
「什么?」
「WOOOOROOOO…」他又咕哝咕哝一次。
「蚝油?」我张大了嘴问。哇,邱先生实在敬虔,连有蚝油吃都要感谢神。
「唉,不是不是,这是猴揉、猴揉!他也大声起来了。
「河流啦!」一旁的姊妹们都听懂了。
停了一秒后,突然大家齐声「哇哈哈哈」地弯腰捧腹大笑。
我笑得最大声。
腼腆的邱弟兄笑得最小声,大概是哭笑不得吧⋯⋯
我的破中文⋯⋯
培训班圆满结束了!一一向同学们道别后,我回到了在地下室的课堂。唉,怎么时间飞逝得特别快?才跟大家熟稔起来他们就要走了。我意兴阑珊地跌回平常坐的位子,顺手拿起一本《人生补羹》开始翻了起来。唉,心里又叹了一声。这些师兄师姊们的文笔真好真美,不仅故事真挚动人,还用了许多我看不懂或念不出的字,像「迷迭」(我念成迷史)、「婆娑」(我以为是婆沙)、(泂泂)〔我猜是回回〕之类的词汇。如果文字营有毕业考的话,这一届的总成绩一定会被我拉下去,成为历届的笑柄⋯⋯
当然,同学们还是爱心满怀地鼓励我:「欸,妳的字跟我女儿的一模一样耶!」(这位阿姨的千金好像是ABC。)
「妳给了我在美国教孩子中文的希望。」(那位妈妈搞不好以为我是在美国出生的。)
其实本人并不是黄皮白心的香蕉,而是台湾土生、巴西长大、美国成熟的变种芒果,内外皆黄。平常大家称赞我的中文好,是因为对我衡量标准太低。这次参加文字营,还往行李塞了一本梁实秋主编的英汉/汉英辞典,又厚又重。练习写作时,全班都用原子笔,只有我一人用铅笔,因为错字太多,需要用橡皮擦。擦的时候,桌子摇摇晃晃;写完后,橡皮屑又堆满桌,同桌的同学们真是辛苦了。连小苏助教(苏老师的大公子)都抱怨:「妳可不可以不要用铅笔写?这样很难拷贝清楚耶!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