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在光中
我與北村有個約

律法只能因人的罪而審判,然而信仰卻能使人的靈魂甦醒、知罪、悔改和重生……
我為中國文壇出現《我和上帝有個約》而欣喜,並期待更多的基督教文學作品出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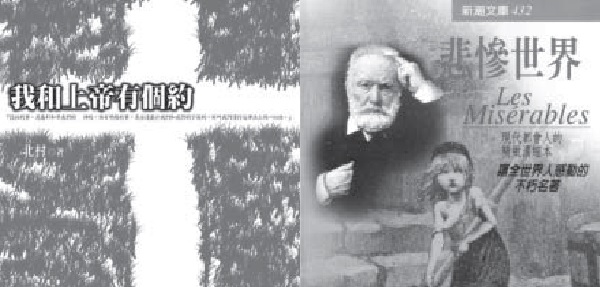
出國多年,閒暇時喜歡看中文小說,內心仍關注中國大陸的文學作品。近二、三十年間,中國大陸產生了許多部優秀的中、長篇小說。信主之後,漸漸悟出好的作家僅僅具備正直豁達的人品、悲天憫人的心靈、飽學博識的素養、高超幹練的文筆是不夠的,若缺乏信仰支柱,作家的靈魂視野便存在殘缺,即使持守著文人的良知和使命,仍然寫不出人性中的崇高和永恆。
北村,以中國先鋒小說家享譽中國文壇。久聞其人為一名基督徒,從書名《我和上帝有個約》可以看出這是一部宗教小說。我滿懷期待地捧起了這本書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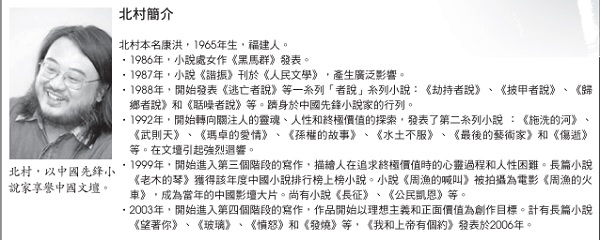
黑暗使人絕望
這部小說情節錯綜複雜,設計巧妙,跌宕起伏。故事以現今中國社會為背景,圍繞一起城市的兇殺案,將這個城市中各個階層中,上至市長、教授、記者和商人,下到農民、妓女、夜總會女郎和兇手等人帶到讀者面前,用敘事手法描寫人性的醜惡與善良、墮落與拯救。
陳步森是小說的主人翁,一個三十歲的無業遊民,靠偷盜搶劫苟且偷生,後因參與一起兇殺案,被捕並受到法律對他死刑的判決。
就以上對此人的介紹,讀者難以給予陳步森同情,甚至會斷定他不過是個罪有應得的人渣而已。然而當我們隨著作者的筆觸走近陳步森的心靈,會發現他和《悲慘世界》裡的冉阿讓(Jean Valjean)一樣,本性純潔善良。陳步森的父親身體殘疾,因無力生存而淪落成貧民,家庭的破碎,將少年的陳步森推向生存的險境。被父母拋棄後的陳步森,在求生的困境中掙扎過、努力過,命運的坎坷和遭遇一而再,再而三地將這位少年推向黑暗的邊緣,最終他走到了社會對立面。
小說深刻地揭露了人性的醜陋和敗壞,以及社會的黑暗。在巨大的黑暗籠罩下,人與人之間因缺少愛和真誠,因不能饒恕和寬容待人,或因仇恨和報復而施害於人。在置身於黑暗又製造黑暗的漩渦中,所有人都成了黑暗的受害者兼施害者。
人物中並非只有陳步森是黑暗所吞噬的犧牲品。市長陳平,城府世故,隨波逐流,喪失正直,因腐敗被追查,陷於恐懼而不能自拔;廉潔的副市長李寂誤被殘害,妻子冷薇受刺激而瘋;主謀兼主犯胡土根是為其受害而亡的父母報仇,而用暴力向社會挑戰。
冷薇身為被害人,因不能饒恕仇人兼恩人的陳步森,心靈受到痛苦的煎熬;同時因恨而被扭曲,並因毆打學生而失去教職。著名的道德學教授陳三立精研儒學,涉獵佛道諸論,卻是道貌岸然,對乞丐缺少憐憫、對人缺少同情和尊重,被婚外情人千葉設下陷阱而身敗名裂……。活在黑暗中的人是罪的奴僕,是在罪的綑綁和轄制之下;黑暗帶給人的是罪性、是墮落、是毀滅、是絕望。
光明擊碎黑暗
如果到此為止,《我和上帝有個約》便同許多作品一樣,停留在揭露社會陰暗面的層次上,停留在深掘人的慾望和隱私裡。於是無論技巧如何天衣無縫,描寫如何驚心動魄,結論只有一個:生命無非是在黑暗中相互碰撞、相互碾壓、相互殘殺,是沒有盼望、沒有意義、沒有價值的。
黑暗的出路在哪裡?
「窗外曙色微茫。行刑的時間到了。蘇雲起和陳步森要分別了。……蘇雲起說,記住,等一下不管遇到什麼,一定要朝著光明的地方去。陳步森知道他是說槍響之後的事,眼淚一下子湧出來。」 1
蘇雲起是何人?作者筆下,他扮演了《悲慘世界》裡卞福汝主教(Bishop of Digne)的角色。他大學畢業後經商,賺了很多錢,也曾經墮落。信主之後變賣資產,成立公益慈善機構─社會公益輔導站,從事心靈拯救工作。
那時的陳步森,已在蘇雲起的帶領下找到了信仰。找到信仰後的陳步森,如同在黑暗中見到光明。他不僅在內心深處徹底地認罪悔改,從因犯罪帶來的痛苦和恐懼中,以及死亡的陰影中釋放出來,因著與神的連接,恢復了人性本該應有的高貴品格,即仁愛、良善、公義、誠實。
首先,多年對母親的怨恨從他內心除去,取而代之的是愛的恢復。對罪的認知、徹底的悔改,使他為了幫助受害人妻子冷薇從精神病症中得以恢復,不惜冒著自己落入法網的危險,判刑之後,為挽救冷薇的生命,捐獻出自己的器官。
律法只能因人的罪而審判,然而信仰卻能使人的靈魂甦醒、知罪、悔改和重生。雖然陳步森在肉體上最終還是得到法律的審判,死亡結局令人悲哀,但是他內在生命改變的見證使許多人的靈魂開始甦醒,讓人們藉著他看到了光明和盼望。
故事結束了,哀傷在寧靜中漸漸散去,化成一片安祥和寧靜。「冷薇望著窗外,好像看到了遠山之上的天空。她想,此刻,他已經坐在天上了。……在這樣的寧靜中,從地上撿起一根草都是美的。」2
詮釋黑暗和光明
聖經新約中,多處論到光明和黑暗,譬如:「你們從前是黑暗的,現今在主裡卻是光明的,行事為人就應當像光明的兒女。光明所結的果子,就是一切良善、公義、誠實。」(以弗所書5:8-9)
在讀《我和上帝有個約》時,總是聯想到雨果的《悲慘世界》,因為兩者有許多共同點:描述了下層人民的苦難,用現實主義的手法,用文學的形式,詮釋了黑暗和光明。《悲慘世界》是講一個釋放的苦役犯受聖徒式的主教感化而棄惡從善的故事。《我和上帝有個約》是講一個死刑犯認識神之後從罪性裡解脫達到自由的故事。
在《悲慘世界》裡,雨果借助卞福汝主教之口,說:「當一個人的心中充滿黑暗,罪惡便在那裡滋長起來。」3當光照在並充實冉阿讓的全部心靈時,他淌著眼淚,泣不成聲。「那是一種奇特的光,一種極其可愛同時又極其可怕的光。……那種光的明亮是他從未見過的。他回顧自己醜惡至極的生活,卑鄙不堪的心靈。」4
在《我和上帝有個約》裡,作者藉著蘇雲起說:「坐牢只能限制你做懷事,不能除掉你心中的罪,只要你從內心認罪,你的罪就被赦免。」「陳步森心中的堤壩終於潰決了,一下子哭出來:我願意認罪……」5 陳步森在給冷薇的信中說:「我現在才明白,我是按聖潔的形像和樣式造的,……我高貴是因為我是按聖潔的形像和樣式造的,……可是,我卻在另一個黑暗的地方活了三十年,……」6
當然,將兩部作品放在一起,並非說《我和上帝有個約》和《悲慘世界》一樣,同是經典傳世之作。
從文學角度省思
我個人認為,《我和上帝有個約》的作者注重人物心理剖析,挖掘人心靈深處的暗角,藉著作品中的人物達到了傳揚和解讀聖經教義的目的,這是應該被借鑑的。但也有美中不足之處。
作品傳達一個信息,世無完人,每個人都是罪人,而每個人犯罪都有緣由。但要給每個人物犯罪的緣由從心理上一一解釋,除了陳步森、冷薇和陳三立之外,還包括輔導者蘇雲起、市長陳平、罪犯胡土根、妓女千葉等等,面面俱到就顯得筆墨不足。
靠人物的大量陳述,人物顯得缺少個性特徵。大段的思想論述,難免說教的痕跡顯而易見。注重人物的思維表現而缺少形體表現,過多地依靠語言表現人的思想會讓讀者感到乏味。其實情節的發展中,人物的一顰一笑都能表現人的思想,沒有詮釋的行為同樣也能反映心理。國畫講究留白,文章留給讀者空間同樣重要。
用TELL代替SHOW,即作者的陳述代替故事本身說話,在一些人物的塑造上面缺少作者和讀者的互動,故事會缺少立體感。倘若增加場景的鋪墊、人物外在的描寫,以及通過人物對話處理,會不會使人物更加活靈活現、人物性格更加豐富飽滿,思想脈絡自然就水到渠成?
身為一個工程專業的普通讀者,我對此書的見解不一定全面,見仁見智吧。當然,挑了諸多不是並非否定作品。《我和上帝有個約》無疑是一部深刻、光明、優秀的作品。我為中國文壇出現《我和上帝有個約》而欣喜,並期待著出現更多的基督教文學作品。
以基督文化做底蘊
每個人受到生活環境和經歷的局限,必然對世界的認知匱乏,基督徒也是如此。文學作品可以間接地幫助我們認識人性、認識社會,彌補我們經歷上的不足;而優秀的基督教文學作品不僅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聖經,更多地認識神,同時了解自我的殘缺。
譬如說,生活的環境中和閱歷裡,不曾近距離地接觸過貧窮和罪犯,我對那群體是陌生的。妓女、罪犯和歹人在我心目中都是臉譜和符號,與墮落、暴力畫上等號。正因沒有生活在社會的底層,正因生活的平順和富足,正因與生俱來的一些良好品性,便更容易表面上謙卑善良正直,內心隱藏著驕傲和自以為義,從而難以將罪和悔改與自身聯繫起來。
《我和上帝有個約》讓我對罪的認知、悔改的功效和得救的確據有更多的認識。書中的陳步森,幫助我們了解與耶穌同釘十字架上的罪犯,何以得救而與耶穌同在樂園裡,為何聖經中說陽光照好人也照歹人。
掩卷沉思:什麼是人的愛,什麼是神的憐憫和慈愛;什麼是人的律法,什麼是神的寬恕和拯救;什麼是活在黑暗中的結果,什麼是行在光明中的生命。(本文图片摘自网路)
注
1. 北村,《我和上帝有個約》,臺北,泰電電業股份有限公司,2006年, 478-479頁。
2. 北村,《我和上帝有個約》,臺北,泰電電業股份有限公司,2006年, 480頁。
3. 雨果,《悲慘世界》(上),中國,大眾文藝出版社,世界名著寶庫系列叢書,15頁。
4. 雨果,《悲慘世界》(上),中國,大眾文藝出版社,世界名著寶庫系列叢書,99頁。
5. 北村,《我和上帝有個約》,臺北,泰電電業股份有限公司,2006年,168頁。6. 北村,《我和上帝有個約》,臺北,泰電電業股份有限公司,2006年,407頁。
 作者小档案
作者小档案
子玉,來自中國大陸,現居美國休士頓。為土木工程師,妻子,三個孩子的母親。忙裡偷閒,識文撰字,追尋遺失的文學夢。驀然回首,筆與夢乃神所賜,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
